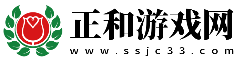【dnf剑魂,为什么我的力量比别人高,但物理攻击却比别人低。】
武器攻击力不如人家的呗,或者没附魔物理攻击
【dnf剑魂转成别的职业属性会降低么?为什么我转成红眼后伤害降低了一半】
我的号也转了几次来回,结论就是,只要有锻造7的武器跟灵魂,伤害不会差别了,当然你得有精通防具
【dnf剑魂为什么更新之后,战力就低了十万左右?更新过后,隔两天打普雷,上线看战力就低了十万?】
战力这东西很虚,也很很多东西挂钩,暴击,技能等级,装备等等,你的装备有没有升级,技能和之前有没有变化,都和战力有关,战力虽然能反映一定的问题,但是问题不大,有的职业战力虚高,所以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DNF剑魂后期攻击低怎么办,刷图时和狂战比明显看出了优势···】
“盲流”部落
吉林省白城地区兆南县兆河乡的保民农场住着一个特殊的男人世界,这个世界的大小就是那一间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放着四条大通炕的旧砖房,而这个世界的全部成员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老汉。准确的说,他们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七十,没有结婚的光棍汉。他们的世界似乎独立与外面热闹嘈杂的一切,除了几位老者,周围的人对他们都是知之甚少,而他们几乎不与外界交谈。据说这些人其实背景不同、身份不一,对于那片土地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外乡人。他们的称号是一个如今我们已经不太提起的名字盲流。对于当地人来说,老汉们拾柴火的身影是他们留给外界的全部印象,而最近人们又隐隐约知道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这个隐没在中国东北偏僻寒冷地带的盲流部落终于要搬迁了。
记者:早啊!大叔。这么早就起来了?
老汉:嗯。
记者:早上一般几点钟起来?
老汉:早上五点,吃了吗?
记者:我们吃了,一般你每天上午几点钟起来?
老汉:我起得早,亮天我不到四点钟就起来了。你们是不是华龙公司?
记者:我们是电视台的,凤凰卫视,你听说过没有?
老汉:凤凰卫视,我听他们传说过。
记者:今年高寿,大叔?
老汉一:他聋了,一点听不到,七十,姓张,张金虎。我七十六。
记者:您上午出去走上一下吗?
老汉二:出去走动走动,锻炼身体,不行了岁数在这儿呢。八十多岁了,你没想想 我还锻炼啥,锻炼也不行了。
在我们进入到这个特殊的部落之前,旁人对他们的描述无外乎这样几种:说他们都脾气古怪;说他们独来独往甚至有人说他们疯疯颠颠。不过当我们真的走进这间大屋的时候,我发现老汉们其实对我们都是相当的热情。
小楠:在这里,我发现没有什么人被人称呼尊姓大名,很多年以来他们都以外号或者简单的姓氏彼此相称。甚至有的人说,久而久之自己原来到底叫什么,连自己也搞不清了。象刚才出现在我们镜头里的那几位,圆脸的那位叫老金;拄个拐仗的那个叫韩老头;戴帽子的那位叫大白菜。对于从何而来,为什么留在了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去,不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提起。
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生活着16个老人,年龄最小的六十三岁,最大的八十七岁。他们清一色是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的光棍汉。老人们大炕的铺位前都建有个人“厨房”,平常都是各起炉灶,而每天拾柴火 做饭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
小楠: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了?
韩老汉:都是自己做。
韩老汉今年87岁,在这个盲流部落中年龄最大,他是一位参加过无数战役的老兵。韩老汉对于过去不原意再次提起,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才同意让我们看他随身珍藏了多年的“宝贝”。
小楠:这个是什么?
韩老汉:解放东北,这个;这块解放华中南;这个是解放华中南的;这个是解放东北的四个丢了两个。
老汉们在这间老屋里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都是操着不同口音,来自不同省份的外乡人。来到农场以前,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但对于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偏僻的保民农场他们却都有一个相同的回答,那就是饥饿。上个世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在经历“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之后,又经历了一个至今仍让许多亲历者心悸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大陆出现遍及全国,在中国乃至世界灾难史上都极不寻常的大面积饥荒。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悲惨的一页,也在盲流部落所有老汉的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老汉:一口人分四两黄豆,你说能干啥嘛。一年两口子拼命干一年还得该生产队,分不着钱,发过三寸布票,三寸布票能干啥,做个裤头还得三尺多呢。我都吃过癞蛤蟆,癞蛤蟆就是蟾蜍;再就是树叶子吧,全都吃遍了,没有没吃过的。像外面植物的东西,没有没吃过的。我的那个奶奶最后也是饿死了,我的母亲走路都晃荡出去地里干活回来(的时候),我家门槛高, 就(拌)倒了。所以我说我出去,省下的粮食就给自己(家里)吃算了。
小楠:你觉得你在家里面是增加家里面的负担?
老汉:嗯,因为我吃得多。
“三年自然灾害”迫使大批农民、城市贫民离乡背井涌向城市、涌向粮食相对宽裕的地区,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自发的人口流动。年青的老金和老仲也加入了逃荒的人流,逃离家乡,逃向东北。
老汉:最启发我的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这个歌,五十年代的时候唱那个歌吧。这个歌对我们启发不小,白云下面马儿跑,描绘这种(景象)。
小楠:嗯,宽阔的大草原一望无际,然后你就出来了?
老汉:我就想去宽阔的地方,当时我有这个想法。家里就像很多猪圈在一个猪圈里,你闯他闯,你拱他拱,拱来拱去就那么大点范围。所以说我就要冲出这个范围,别处无门了,根本就没办法。逼上梁山也得闯关东,只要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来你一个人。二十多岁,带了二十三块钱,带两个大煎饼,我到(正月)十六拿点干粮就走了。我哥给我五块钱、贰斤粮票,就到了外面上了五毛钱的车,一直开到济南。
老汉们大多身体很差,如老王的气管炎、腿浮肿,老苏的关节炎,犯病时,止痛片也得省着吃。大多数人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有更多的走动,白天除了到附近捡点柴火、垃圾就在房里呆着或者晒晒太阳、听听收音机。他们最宝贵的财产大都是一台放在耳边才听得清楚的老收音机。
小楠:你这电视还能看吗?打开我们看上一下?
78岁的老王无论冬夏总戴一个蓝色的帽子。他在一次农场劳动事故中失去了右手,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晚上有时憋得喘不过气来,要跪卧着才能睡着。老王捡垃圾捡回来这台黑白电视,是老屋里最贵重的一件物品。
老王:效果就是这样了,只能收一个台。嗯,一个台还效果不好。
小楠:对于当年从家乡出来逃难混口饭吃的老金和仲老汉来讲,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身无分文离开家乡村口的那一刻,他们已经走入了一种新的身份。
一九五二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要“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于是盲流概念正式产生。而随后的几年中,虽然老金和仲老汉并不知道盲流二字为何物,还是报着逃一条生路的希望汇入了这一条茫然涌动的人流,踏上了不知方向没有终点的路程。而当他们最终踏上东北那片土地的时候,他们这种身份又有了一种新的注解。因为东北人按照他们的语言习惯在
盲流这样的的词后面加上了一个轻轻的后缀。于是从此他们便成了众人眼中的“盲流子”。
老汉:盲流, 这个盲流字吧。盲不就代表瞎子,是吧。这个不用给你们解释,你没我们理解得透。这不盲目流窜吗?所以说这两个字,我感觉说来说去,我不反感。
小楠:当时你真的没有目的?
老汉:没有目标,出来谋求生活,你知道哪儿能留住你,你知道哪儿是你藏身之地。来到东北 ,举目无亲,两眼黢黑。到东北我第一脚是在一个生产队里,还不如他们的条件呢。就一个被炕,给人家生产队干活,那时候吃人家留着喂牛的饲料。就说你们在外面要饭,背那么大的行李也找不着活儿。我也要过饭,饿得肚子不行,偷也不会偷,抢也没那个胆子。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帽子都拍碎了,头上全是虱子。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及之后几年,为了解决大量盲流四处流动,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吉林省把各地被多次收容,不愿回乡或生活没有着落的“老盲流”强制分批集中安置在省内的几个劳改农场。其中,安置最多的是位于吉林省西北角的保民农场。前后安置在这里的“老盲流”最多时多达到五、六百人,年龄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而老金和仲老汉就在其中。一群来自全国各地展转漂泊的老少男人,终于在中国东北的小县城里落下了脚。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是身份不明来路不清的异类。所以可以想见,当年围绕着他们的肯定是不尽的揣测和深深的戒备。于是,男人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且是非常封闭的世界。其实在那时候,在他们的心理,他们大都觉得这不过是个暂时落脚的地方,没有人想到会在在这呆上一辈子。也没有人想到象,他们这样一群年付力强的小伙子会在这里,就是在这间摆放着大通铺的房子里相望着老去。
老汉: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场里的领导到农村就说了“这些人都会偷,不能接近他们”。所以老百姓不敢接触我们,见我们都躲了。那时候我们有集体去干活的,人家也都不往这里凑。
人家哄小孩说:“别哭了,来狼了”;这里哄小孩说“别哭了,来盲流了”。小孩就一声不哼,马上就像来了狼似的吓唬住了。他们认为盲流子是什么呢?就是调戏妇女的流氓的。这个流子国家安置在这儿,就是长期流浪不回家的流子,没有地方去的流子。他们认为流盲就是强奸妇女,横行霸道的这个流子。只要谁知道我们是盲流子,到那里就不太痛快了。你到哪个地方,谁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还能抬起头来。要是知道说你是盲流子,就赶紧要缩回来。
小楠:你们听到当地人这样叫你们盲流子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老汉:当时认为国家安置到这里来了,再说出去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在这里。盲流子就盲流子,反正我们自己清楚,比劳改教养强。
状态记录:当年可能是一个屋里,达到最多的时候一百多人吧,基本是在六一年或者六一年以前六零年,一直到六五年、六六年这个期间。这一百多人怎么住呀!一人就这么大个地方,公家给一个小被窝,一人多大一个地方,就这么大,也就五十公分,有这么宽吧,就一床被子叠的四四方方的,一个挤一个、一个挤一个。反正忙的时候基本也没有休息的时间。
小楠:能自由的出去吗?
老汉:自由出去是这么说,最严的时候,像现在的油库那儿,都不让过去。走到油库回来你就检讨检讨你是什么思想。以前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还念毛主席语录,早上起来早请示晚汇报。
当年到农场时,每个盲流一个月两元钱,吃穿免费。老汉们说,他们那时打心眼里感谢毛主席,感谢。因为在经历了长时间饥寒交迫的流离后,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落脚,有饭吃的“家”了。
小楠:老汉们最近心情都不错,因为他们很快就要离开老屋了。不久前一家长春媒体的记者来到了老汉们很少有人光顾的老屋,看到他们的状况后,和长春一家养老院联系,准备把他们接到长春去养老。
老人告诉我们,那个记者前两天捎信通知他们,今天、最晚明天就可以搬家。他们已经卖了还值点钱的东西,扔了破旧的衣服,就等长春的记者来接他们了。
小楠:你知道要走了吗?
老汉:知道。
小楠:想离开这儿吗?
老汉:那怎么不想,已经不想呆在这了。
小楠:不想呆在这儿,为什么?在这间房子里面你们是生活了几年了?
老汉:四十一年了。
小楠:那很快就要离开这儿,心里面怎么样?
老汉:哎呀!我乐呵呵的。我到哪儿都是家,哪儿都是我家,这么大国家,党就是我妈妈了。
小楠:对老金和仲老头们来讲,似乎是突然在某一天,他们的部落里加入了一些更加陌生的人。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看起来知书达里的城里人是因为什么被发配到了这样的地方。他们也无法猜透这些看起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在革命群众眼里何以如此罪孽深重。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在这样的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似乎是带着原罪的盲流们和这些被唤作是右派的人,这些互不问过往的陌生男人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大灾大难,而这灾难现在想来仍然是触目惊心。
保民农场当年是一个劳动教养农场,盲流安置前就关押着几百名“右派”,“右派”和“盲流”在这个农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群落。
小楠:彼此之间,身份都知道你以前是哪儿来的?
老汉:那不知道,都不知道。反正这么说吧,吵架的时候瞎估计吧。右派年龄大一点,一般的有点文化吧不会和人家吵。反正就是干活不好,开会的时候能提个意见啥的。
小楠:这七百多人里面,有多少右派你们也不清楚不清楚?
老汉:不清楚。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这个偏僻农场的“盲流”和“右派”也都没能幸免,他们共同经历了一场灾难。在“文革”期间,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就有二十多人被打死或。他们死后,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右派”还是“盲流”。
老汉:那个杨东升,闹情绪,别人都上工去了都走了他还在那躺着不起来。我拿鞋给他穿上,两脚一踹又跑炕上躺着。我还没走呢,人家文公武卫那个就来了来了几个人,从炕上拽下来。 然后他说:“不要拽,我自己穿衣裳,自己穿鞋。”那知道就没有好,自己把平时喜欢的衣服,手上还拿着蓝梆子白底的球鞋穿得整整齐齐的,好好的,就下地下,很从容的跟着走了。到游斗完晚上回来,在前面有一个小土房,晚上就没气了。我在那里亲眼看,很从容地走,一点没有惧呀,不就是说游斗嘛。人家从炕上下来走,当时我心里就想:跟上刑场一样。
如今我们在农场里已经很难再问到右派的身影,据说他们走的走,死的死,留下的一两个也因为精神失常再也没有人能说得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老汉:不因为啥,看你不顺眼,把你揪出来,揍不死你就揍不死你,没商量。
记者: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说说文革的时候。
老汉:刚才我第一句话态度阐明是非人生活嘛,咱们过得不是人的生活。
记者:死了多少人。
老汉:死了的多,因为啥呢,后期我回家了,我在的时候打死有十来个吧,抓到厂部那个院子中间,穿着白布衫,白白的,就那个现在四轮车的橡胶带,带钉了那么长的木头把,那叫二龙吐须吗也不知叫什么,钉两个胶带,打得满地滚,没有多厂时间,白衬衫,整个就是红的,你想出了多少血,他还行,没打死。再就是韩宏山和那个朱学贵叫人家打的,暴起来那个皮和那个血疙瘩……(右派)大部分死了吧,回家的,年轻的回家了。留到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大部分都死了。后来右派平反了吧,那几个平反的,有的回去了,有些都死在这个地方。
记者:有些右派都死在这个地方。嗯,平反以后死在这个地方。
记者:我看你们把一些东西都扔了。
老汉:现在扔掉多半了,原来这床上这么高,该卖的卖了,原来就这么高,半米吧。有半米吧。
记者:半米(高)都是些什么东西。
老汉:破铁,柴火,木头,什么玩意儿都有。
记者:你们听说要走挺高兴,就把那些该扔的东西扔了。
老汉:都扔了。别的都卖了,水桶啥的都卖了,养老院他们不让拿,我拿来干啥呢。嗯,你不卖拿来干嘛,多少反正挣点钱。
记者:拍一个你们的全家福。你们最后一次了,在你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屋子里面。都要走了,总共有多少人?
老汉:总共是十六个人。
记者:在这个屋里面,大家都相互了解,身份都是一样的,盲流子,都是一辈子的盲流子。一辈子的盲流子。所以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老汉:嗯,都这么,反正你说我我说你,你说我两句,我说你两句,就这么着。
记者:在家里面,回到家里面,回到人群当中,是什么感觉。
老汉:就因为娶媳妇把我撵回家,呆了十三年,说有娶媳妇的,全给你撵走,不行。
记者:为什么要撵你呢。
老汉:不让你成家,好像现在劳改犯一样,没有娶妻结婚的权利,剥夺权力了,就这个意思,很简单一句话,撵走不少呢。他能知道,这不都在家全撵走了吗,我媳妇头一个孩子都临产了,还不让你生,把我留在这块儿,媳妇自己回去,回家头一个孩子没生下,那个孩子因为啥,因为坐车,一个是晕车,再就是条件也不行,就把小孩活活的流产了。
记者:分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老汉:那还有什么,那能不惦记吗,当时的心情吧,这事儿吧,我告诉你,四十年,一言难尽,那里面复杂的事,简直一句说不清。我就留在这儿改造改造,做个正常人,改造改造,领导认为好的,当工人的就是好的。
记者:上面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时候是改造好了。
老汉:那个不承认,改造好不好,领导认为,看你改造的好了,他就表扬表扬你,或者好的可以变成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劳模,这都是领导的认同。
记者:说你改造好了。
老汉:嗯,就好了。
记者:你就可以到农场里面当农场职工?
老汉:嗯,对,改造好了当个职工啥的,这就是最高的盼望了。
记者:你们就盼望着这一天,领导给你们说,你已经改造好了。
老汉:嗯,改造好了,上别的地方干了,有给你介绍对象的,有给你弄个屋给你住着的。这就算是改造好了。
记者:你看这个盲流子的话,这个帽子,这个称呼,伴随了你大半生。
老汉:就是大半生,就在能干的时候,这就是大半辈子,后来老了,你说是盲流子,你说我是犯人怎么的,也不想挣钱了,也不想成家了,你爱说啥就说啥吧,就说劳改犯也行,就这么一个人呗。
记者:你对你这一生这样过下来,觉得值得吗。
老汉:最后我看值得。
记者:你后悔你当初的那种选择吗,为了省下一口粮食。
老汉:那个不后悔,一点都不难受。我觉我觉得我到什么时候还是我,还是我。
记者:为什么呢。
老汉:现在我闺女是大学生,还可以吧,盲流的后代能考上大学,不是像原来像我们那个年代,硬件生活,各方面啥的,我也不缺啥,人的一生乞求啥呢。
记者:那你现在听到他们叫你盲流子,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老汉:我毕竟是我,凭两只手,你看我的手,看看,跟你的手比一比。好像一个名字,叫名字的好坏,是个代名词而已,你说盲流,我也没有盲,也没有流,你愿咋叫就咋叫,不管他们怎么小瞧我,我认为自己不那么太渺小。
到我们节目播出时,最后的“盲流部落”并没有消亡,十六个老汉仍旧住在已经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屋里,等待着长春方面的消息
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
【DNF曾经最火的剑魂,现在处境怎样?强度如何?】
DNF100级版本比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玩家不需要特别高的打造,就能够进团体验毕业副本。低门槛让希洛克里时常发生“故事会”,这些故事会里的主角往往都是剑魂,曾是DNF的排面职业,打团却人人喊打,不让斩钢不准抢DPS,如今的剑魂比当年的红眼阿修罗活得还卑微。
前不久又因剑魂闹出了打节奏,因为打团时候剑魂玩家放了个大拔刀,就被队伍里的大佬指着鼻子骂。事情经过并不复杂,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剑魂进图看见有小怪立刻就放了大拔刀,这时候主C红眼不乐意了,当下就认为剑魂是在抢DPS。
于是直接就在聊天框里开始了“抒发感情”,剑魂玩家看完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难道自己连大拔刀都不能放了?
之后这名剑魂玩家也是展示了自己的打造,一身红10的装备却只有4591的力量,难怪被主C怀疑用大拔刀抢DPS。因为当前的副本比较简单,在满足了最基本的通关需求以后,玩家自然开始向着“排面”努力。而在DNF里,牌面就是DPS数据,谁占比最高,谁就是“大佬”。于是技能出手快范围大的大拔刀,自然就是抢DPS的不二之选,因此放大拔刀的剑魂很容易成为被声讨的对象。
不止是抢DPS的问题,国服剑魂还因为“斩钢式”这个技能,而被扣上了“钢铁侠”的帽子。因为可以切换34和纯C,所以很多剑魂在看有其他34跟自己互保的时候,往往选择损人利己的切斩钢。这些极个别玩家的做法,让剑魂整体风评急剧下降,甚至有玩家直言,打团能不组剑魂就不组剑魂。
大拔刀抢DPS,斩钢迫害其他34枉顾组队收益。这两个玩家最深恶痛绝的点都聚集在了剑魂这个职业上。于是就有玩家说出了“白手就是原罪”这句话。现在就连正常的剑魂玩家想斩钢当纯C,都要低声下气小心翼翼地问过才行,大拔刀更是不敢清小怪。
学了技能不让用,斩钢斩铁也得看人脸色,不知各位剑魂玩家如何看待?
【DNF剑皇50万战斗力属于什么水平?】
正常的,剑皇起码30战斗力起步,加油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