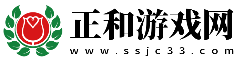【小说忘记名字了,内容大概是一名士兵穿越到明朝,从一明盐贩头目,慢慢当上总兵,最后当上皇帝】
八卦神门阵 攻破八卦神门阵即可获得蟠龙枪
开始进入阵法的进法 是远程攻击类,策士类,骑兵类,步兵类,前4个人是这个顺序 进入后 后面随便进
进去后 我军回合出现敌人 攻击敌人顺序为步兵、骑兵、策士、弓兵,顺序不可变 就是在步兵类 全部消灭以前 别的阵里的敌人不能死光 依次类推 策士那阵 多用威吓和混乱 是最麻烦的阵
太极站位:那几个村庄周围有隐藏的村庄地形,排列成太极图案 看下面有图 注意在2个兵营中没有站人以前 其他位置不要全部战人 否则会降低状态
十面埋伏阵打法:一类一类灭,比如:想先灭骑兵的话,在四个骑兵没有全部死掉之前,不要让其他敌人死掉,只能灭掉一类之后再灭一类
用杨排风 杨延德 孟良 牵制住一面的敌人 攻击力强的人 去另一面 按分类消灭 敌人 可以混乱住敌人的炮车和文官单位 就是麻烦点
【明末清初各大历史事件】
鉴于篇幅只写明清之间的斗争,
万历二年,明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反叛,辽东总兵李成梁诛之,王杲之子阿台章京逃脱,于万历十一年起兵叛明,李成梁收买女真内奸,里应外合攻破古勒城。误杀努尔哈赤之父。努尔哈赤对明怀恨在心,集齐十三副盔甲发誓报仇,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父交好,选择性放任努尔哈赤,使努尔哈赤在明朝四十万重兵眼下逐步壮大,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克图轮城,甲板城,万历十二年下兆佳城,活捉明将李岱。万历十三年击败女真苏克苏潕部,董哲部,大胜于吉林崖。万历十四年攻鹅尔浑,万历十五年破女真哲陈部,万历十六年统一建州女真。
万历二十一年征服纳殷路,珠舍里路路。于古勒山大败海西女真部。由于海西女真实力强大,努尔哈赤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至万历四十三年统一海西女真,万历四十四年即汗位,建立金国(后金)。至此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反观辽东明军却基本未有大的军事行动,对于把辽东作为为军事要地(军管区)的明帝国来说显然是不正常的,那么最明显的解释就是辽东的李氏家族隐瞒了努尔哈赤在各地的进攻行动,其动机至今不明,有可能是以匪养军(以此向朝廷要钱),也有可能是所谓的亲戚关系(李氏与努尔哈赤有姻亲联系)。
古人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总之帝国失去了消灭隐患最好时机。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布《讨明檄文》,率步骑两万向辽东各地明军进攻,克抚顺外围屏障东诸堡和大都,数月后攻克抚顺,并对抚顺进行了屠杀。沈阳,锦州因有重兵把守,金军感到实力不足因此从抚顺退却。此战震动了明帝国,帝国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率二十余万兵马平叛
这就是萨尔浒之战的开端。萨尔浒之战失败其实对于整个帝国的硬实力影响并不大,在硬实力上改变不了明强金弱的局面,这场战争对帝国的破坏在于人心上,倘若迅速作出反应派得力干将主持大局,明军仍可一战,但帝国却忙于党政内斗未及时作出反应,这导致战败后帝国在辽东军心尽失,短短数月上百个堡垒内的明军不战而逃,辽东各卫所已成空城,各地总兵为了逃命甚至驱赶百姓拆毁城池。这造成了可怕的多米诺效应,辽东拥往关内的汉族难民多达几十万人,随后努尔哈赤攻占铁岭和开原,明军在关外的坚城仅剩沈阳,至此明帝国从太祖朱元璋以来在辽东二百余年的经营基本告吹,天启二年努尔哈赤进攻广宁,因将领孙得功叛明,明辽东巡抚王化贞战败,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又无军队,只得率数十万难民入关。至此明军丧失辽东全境。
天启二年明帝国启用礼部右侍郎孙承宗,加封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委派处理辽东事务,孙承宗亲自赶往山海关,并多次冒险前往关外,最终采用了类似于唐代清剿突厥的战略,即建坚城为战略支撑点,军队屯田建堡作为屏障,立新军(辽军)为机动力量连接各个战略支撑点,结果证明这种战略极其有效,短短四年孙承宗收复了几千里的失地,有效的杀伤了后金的有生力量,并基本建立了关宁、宁锦防线。再此期间明军虽未发动大规模战役,却基本重新在辽东站稳了脚跟,因此孙承宗不论是在《明实录》还是在《明史》中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登莱战役 后金占领辽东后帝国与辽东半岛的联系基本中断,通政使袁可立上书言“登莱唯北岸旅顺口,实咽喉之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于是天启二年,授予节钺巡抚登莱,当时登莱玈顺早已沦陷袁可立率家丁前往,遇匪寇袁可立单骑入阵,袁可立到任后数月内组织优势兵力,从海上突然登陆,调度两镇兵马奇袭金军,以皮岛总兵毛文龙为侧应,并以反间计策反后金女婿刘爱塔。收复金、复、盖三卫和旅顺,取得东江大捷,基本摧毁了后金正蓝旗。该战可谓明军反击战中最漂亮的一战。
柳河战役 天启五年山海关总兵马世龙从生员刘伯襁口中得知金四贝勒皇太极入驻耀州,且兵不足三百,马世龙大喜统关内兵从娘娘宫渡河偷袭耀州,结果行迹败露,遭金军突袭,原定的觉华岛侧应兵马也未赶到,结果中军李应科先锋鲁直贾战死,明军兵马折损半数。
天启六年,督师孙承宗遭魏忠贤陷害,高第接替孙承宗的职位,高第贪生怕死,不请示朝廷擅自拆毁城池,撤回兵马,辽东再次失守。
宁远战役 天启六年高第撤军,时宁远守将袁崇焕拒不撤离,当年一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袁崇焕给三面城墙各拔一万守军,自率一万兵马坐镇中城,努尔哈赤连攻数月不下,因明军火炮众多反而自身伤亡惨重,(努尔哈赤本人也极有可能受重伤)五月金军死伤过多(《明史》说死伤三百人,但后世保守估计在八千人以上)因而撤退,七月努尔哈赤去世。
宁锦战役 天启六年袁崇焕出任辽东巡抚,高第被弹劾,后金大汗由皇太极继承,同年袁崇焕派人与皇太极议和,实者为重新恢复宁锦、关宁防线争取时间。而皇太极也趁机一举攻陷朝鲜平壤,解决了后方。双方都在为即将的大战做准备,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借口明军在大凌河筑城,率旗军十二万攻明。五月初金军抵达广宁,明军收缩兵力退入锦州,金军合围锦州,总兵赵率教正在锦州监督筑城,于是率领明军坚壁清野,坚守城池,并不断假意投降,以拖延金军。总兵满桂也不断派兵截取金军粮道,骚扰金军。五月末金军连攻十五日不下,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而明军迟迟不派主力来援,也使金军围点打援的计划落空,皇太极只得暂时放弃锦州,向入关必经之地宁远进攻。袁崇焕守中城,总兵孙祖寿、许定国守西面,祖大寿守东面正面使用火器打击,两侧包抄分割金军,最后以关宁铁骑正面冲击。金军大败,皇太极的堂弟被打成重伤。皇太极只得退兵转攻锦州,结果又遭赵率教痛击,减员无数只得退兵。此战明帝国举国欢庆。
丁卯之役(此战争议较大且主要是后金与朝鲜两方,这里只节选与明军有关部分) 天启七年正月后金六王子率军四万进攻铁山,大王子阿敏攻云从岛,毛文龙于正月十五日夜夜袭阿敏部斩杀数百人,但自身也伤亡七百多人,十七日又杀死了两千多女真降兵,阿敏没有船只只得迁怒于朝鲜,毛文龙又伺机跟随,先后偷袭斩杀近千人。但毛文龙的说法于诸多史料不符,不仅是清人史料,就是朝鲜史料也与其相左。
己巳之变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复出,崇祯二年后金之主皇太极携蒙古军,总数共十万绕道蒙古高原,从山西进入中原,期间屠杀了十几万百姓,袁崇焕奉命回师,但一直却不出动主力部队,由此被朝中重臣和后人诟病,但实际上袁崇焕是在寻找战机,从前面多次战役来看,若想获胜明军只有坚城固守,而此时袁崇焕心中的坚城正是北京,但袁崇焕显然没有他老师孙承宗的战略眼光和头脑,都城的意义是不允许它作为挡箭牌的,在崇祯的多次命令下,袁崇焕终于越过金军,驰援北京。但他却要求率军队进入都城,随即要求便被驳回,袁只得驻兵城外与金军鏖战,在祖大寿、满桂、刘应国等人的全力配合下终于击退了金军,但明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却遭到了严重破坏。
松锦之战 崇祯四年皇太极借口祖大寿诈降,向锦州发动进攻,若取山海关必先取关外四城(松山、杏山、宁远、锦州)而四城之首便为锦州,初战祖大寿偷袭清军,击败进攻宁远的多铎,皇太极吸取久攻宁远的教训,制定久围孤城,而后劝降的策略,在宁远修建的义州城,并在汉军旗的建议下于义州屯田,义州成了进攻的前哨阵地和清军的补给大营,又在锦州城外掘地三尺,修建栅栏营寨,营寨中又挖深壕。皇太极暗中与城内蒙古人相联系,城内蒙古人乘机作乱,内外夹攻下锦州外城失守,余部明军退入内城。祖大寿只得向朝廷告急,崇祯命山海关总兵洪承畴与另外七大总兵援助锦州,敌军势大当以步步为营,静观其变,但朝廷却粮饷难继,命其速战速决,于是洪承畴命十万兵马只带三日粮草,洪承畴不携带全部粮草意思是即可以给自己留有退路,也可以给朝廷一个交代。但这个决定将把明军送上绝路,在清军多路设伏和堵截下,明军撤往松山,粮草多屯于笔架山,但也有力的打击了追击的清军,皇太极对失利感到气愤,于是率主力应战,并趁决战时,突袭了明军的粮仓笔架山,笔架山上明军火器众多,本可与之一战,但守将却率先逃跑,导致军队溃败,笔架山失守,眼看粮草断绝,明军主力军心惶惶,洪承畴命令分头突围,吴三桂等人突围至杏山城,洪承畴本人突围未果,于二月十八日被活捉,五月剃发降清。松锦战役明军完全失败,标志着辽东防御体系的崩溃,至此帝国在辽东再无精兵。
宣大抗清 崇祯九年九月,清军沿大同、宣府入侵,劫掠京畿地区,清军将汉族女子浓妆艳抹载于车上,挂起“各官免送”之牌,以此侮辱明军。但明军畏惧野战,各地勤王之师均游弋于京师附近,却拒不迎敌。崇祯只好召回正在东南平乱的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卢象升,再赐尚方宝剑,以总督三军。京师解除警报后,鉴于辽东局势已尽皆糜烂,明廷令卢象升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此时宣府、大同形同虚设,卢象升到任后屯田备粮,修整城墙,期间多次击退了蒙古乞炭的进攻。崇祯十年五月,清军攻击山海关,摧毁了山海关正门,杀死明总督吴阿衡,并将进攻的前哨阵地推进至牛兰。崇祯再次召回卢象升,并第三次赐于尚方宝剑,令其总督天下兵马,但实际上受卢象升节制的兵马不过两万。崇祯十年八月皇太极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大将军、贝勒岳拖为扬威大将军、贝勒杜度为为副相,分两路伐明,并从密云方向突破了长城,并驻军通州。崇祯十一年卢象升进军至巨鹿,关宁铁骑在鸡泽防守,卢象升派人协调关宁兵马,但因为所属兵马过少,关宁军拒不接受卢象升的调遣,明军互相掣肘一时难以发起反击。当时孙承宗因屡遭诋毁只得辞官,正赋闲于老家高阳。清军得知后进攻高阳,并多次派人劝降孙承宗,孙承宗拒不理会并组织城中百姓守城,十一月清军发动攻击,高阳百姓上至老叟,下至妇孺皆以砖石抛击清军,城破后,清军俘虏了孙承宗,孙承宗则面向北京方向行九拜之礼,而后自尽,其族人皆被屠戮。消息传回北京,崇祯拊手痛哭,而卢象升也万分惊讶,此时卢象升决意以死报国,十二月卢象升进兵至蒿水桥,遭遇清军主力,卢象升以虎大威为左翼,杨国柱为右翼,亲领中军架设大炮,与清军进行野外决战,战斗从清晨进行至黄昏,明军兵力远不如清军,关宁兵马也拒绝来援,卢象升的士卒俱死伤,而清军也感叹从未遇之野战能力如此之强的明军,最后清兵围之数匝,卢象升知必败无疑,按剑大呼:“将军死绥,有进无却”,随后跃马冲入敌阵,身中四箭三刀血流而死。宣大抗清是明帝国与清廷的最后一场大型战役,此后帝国基本丧失了对北方的控制力,帝国的灭亡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
清军入关(以下按照清朝年号讲述) 顺治元年清廷调集满、蒙、汉三族军队,几乎倾巢而出,由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南下,当年四月顺军攻破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至此“明”作为全国性政权的时代被终结,多尔衮得知后本想按照原来路线继续进军,却在此时突然接到吴三桂的降书,于是立即改变方向,朝山海关集中兵马,并打出为明复仇的旗号。此时驻守山海关的一支明军投降了顺军,因而吴三桂与顺军发生激战,顺军援军抵达山海关西罗城,吴三桂即将兵败,清军于是疾驰南下,吴三桂开关迎清,在清军的帮助下迅速的击败了顺军,至此山海关门户洞开,而李自成在北京再次称帝(在一月份李自成已在西安称帝)后仓皇出逃。十月清军攻破太原、晋东南、长治,十二月潼关失守、大顺都城西安陷落,顺治二年四月兵败九江,五月李自成被湖南山民杀死,大顺灭亡。由于大顺没有完善的官僚体系,加之多年以来对中原地区大加破坏(义军每过一城就要拆毁城池,焚毁全城),致使顺军几乎没有坚城可依,李自成又越来越多疑噬杀,最终大顺政权迅速瓦解,但就阶级斗争意义上来说李自成确为一代枭雄,对其也不必过于批评诟病。而清军入关则为日后统治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民族大融合 顺治十八年吴三桂入缅,摧毁了南明永历朝廷,至此由多个明朝宗室建立的流亡政权的总称——南明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当时各地的抗清活动仍就此起彼伏,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激烈,清帝国统治者则对汉蒙人民非常戒备,这种局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改变,至乾隆朝明末交替战争已过去百余年,汉满民族矛盾弱化,帝国统治者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正式提出编纂《贰臣录》《奸臣传》《忠臣列传》,对明末时期诸如孙承宗、袁崇焕、史可法、卢象升等抗清名将大加褒扬,录入《忠臣列传》,并肯定了扬州、嘉定军民在明末抗清中表现出的气节,对吴三桂等先降后叛之流录入《奸臣传》并对其严加批判,对洪承畴、钱谦益等则录入《贰臣录》对其则极尽嘲讽之笔。直到这时清帝国上层才真正意义上完成从外来者到帝国统治者的思想转变。
【求穿越明末为崇祯皇帝,或崇祯皇帝的儿子的历史小说,最好是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有深度,救了明朝,那种】
明帝。现代人朱影龙穿越到明崇祯皇帝的故事,如何从一个小小的信王慢慢到达权力的巅峰。文笔还算不错。
【明朝末年如果把崇祯换成朱元璋的话,明朝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
傲视神泣还不错、开了7区了。之前的区还有人、而且承诺不会关服
【端午忆屈大夫,难知,生逢乱世满经纶,怎奈小人嫉几分纵身一跌逍遥去名垂千古有几人!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回】
“香草美人”的奥秘 [返回]
--------------------------------------------------------------------------------
文:舒芜
抗战时期,有一位孙次舟先生发表文章,考证屈原实际上是个“弄臣”,是龙阳君一流人物,引起众论哗然。闻一多先生当然也不赞成这个新奇之说,但是指出它倒也事出有因,就因为屈原辞赋确实是“男人说女人话”。中国文论向来说屈原辞赋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清代常州词派主张“托志帷房”,自称这是“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究竟什么是“香草美人”,什么是“托志帷房”呢?闻一多先生这一句“男人说女人话”把它解释得通俗鲜明,叫人一下子就记得住。我从那时起,常常思索:究竟这种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普遍不普遍呢?促使我这样思索的,是因为我读李商隐诗,极不同意有一派注解把李商隐那么好的爱情诗即“无题”诗一类,一概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身世感遇”之作,解释为巴结令狐綯而巴结不上的乞怜之作,我以为这种解释很煞风景,中国缺少爱情诗,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李商隐,何苦硬要把他最有独创性贡献的爱情诗解释成庸俗的仕途奔兢之诗呢?李商隐在仕途中原也是庸俗的,所以他也有“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那一类巴结贵官而巴结不上的牢骚,但是他既能如此明说,又何需用“托志帷房”呢?(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乃是男性追求女性之诗,并非写女性对男性的恋慕之诗,又是一大问题,此不详论。)我自信关于李商隐的看法是不错的,但是我不能否认此外确有不少诗人词客都有男人说女人话的时候,例如最著名的“未谙姑食性,先倩小姑尝”,“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之类,的确都是借男女之情,寓名场仕途之事,我不能否认《闺怨》《宫怨》一类题目几乎没有几个诗人不曾做过,而他们之所以要作这些题目,都是借以抒自己之怀,只有极少数例如白居易的《上阳人》那才真正是哀妇人而为之代言。于是,我承认“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确是相当普遍的,尽管李商隐的爱情诗并不属于此类。
跟着我思索:为什么会这样?男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话?多年以来,我想出了一些道理,直到前些时,看长春出版的《文艺争鸣》双月刊一九九三年第五期,上面有周乐诗的《换装: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女性写作传统和女性文学批评策略》一文,我觉得他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比我想到的深刻得多。他根据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关于现代社会既是“菲勒斯(男性)中心”社会,也是“逻各斯(语词)中心”社会,二者复合为“菲逻各斯中心”的理论,认为还要看到社会多重权力压迫系统的结构,这才能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即“男性作家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的反常现象。我很赞赏“男性作家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这一提法,这指的就是“男人说女人话”,它是对这一现象的更精确的理论性的表述。周乐诗的文章列举屈原、宋玉、曹植、辛弃疾诗词中男人说女人话的许多例子,关于辛弃疾,他说:“即以豪放风格见长的辛弃疾也有如许忸怩的词章:‘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摸鱼儿》)。”这说得很有趣。周文从理论上说明道:“自拟闺中少妇娇媚幽怨的诗词,频频出现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当我们进入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秩序时可以发现,因为他们受到王权统治中心的压抑,这种受压抑的处境使他们在进入‘菲逻各斯中心’系统时,被贬入以女性作为象征的客体地位,因而男性作家被迫使用受压抑的女性话语。……君臣、父子、夫妻等组成一对对二元对立的统治被统治的等级压迫关系。班昭在《女诫》中云:‘(女人)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这样,男性诗文中君臣之遇的关系,便与表现男女感情的各式主题形成对应意义:渴望报效—相思;怀才不遇—美人迟暮;为君王重用—宠幸;受冷落—薄情;遭排挤打击—弃妇。这样的理解,男性作家笔下众多的闺怨诗文便有了着落。”这就是说,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男性作家在君臣关系中被统治受压抑的处境,与女性在夫妻关系中被统治受压抑的处境相同,所以易于通感。男性作家作为男性,在“菲逻各斯中心”的秩序中,能找准的位置就只有统治压抑之下的女性的位置,所以他们只好委委曲曲地说女人话。这种解释,是相当深刻的。
但是,我再细想,又觉得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男人说女人话,仅仅是消极的被迫,而不是一种积极地主动地选择吗?没有艺术表现上的必要吗?如果纯粹出于被迫,那就应该所有男性作家一概都只说女人话,事实上,并非所有男性诗人词客的集子里只有“闺怨”“宫怨”一类题目,他们说男人话的时候还是占绝大多数。那么,究竟什么时候他们才要说女人话呢?有什么艺术上的必要呢?于是,我找出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来看,这是常州词派的词论的代表,看看他对于“托志帷房”究竟是怎么解释的。
《白雨斋词话》卷五第二七条(标码据人民文学版,下同)云:“蒿庵《蝶恋花》四章,所谓托志帷房,<SPS=0384>怀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阳依绿树。门外斑骓,过了偏相顾。玉勒珠鞭何处住,回头不觉天将暮。’‘回头’七字,感慨无限。下云:‘风里余花都散去。不省分开,何日能重遇。凝睇窥君君莫误,几多心事从君诉。’声情酸楚,却又哀而不伤。次章云:‘百丈游丝牵别院。行到门前,忽见韦郎面。欲待回身钗乍颤,近前却喜无人见。’心事曲折传出。下云:‘握手匆匆难久恋。还怕人知,但弄团团扇。强得分开心暗战,归时莫把朱颜变。’韬光匿采,忧谗畏讥,可为三叹。三章云:‘绿树阴阴晴昼午。过了残春,红萼谁为主。宛转花旖勤拥护,帘前错唤金鹦鹉。’词殊怨慕。次章盖言所谋有可成之机,此则伤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云迷洞户。不道今朝,还比前朝苦。’悲怨已极。结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侬和汝。’怨慕之深,却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谗人间之,故无怨当局之语。然非深于风骚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残梦初回新睡足。忽被东风,吹上横江曲。寄语归期休暗卜,归来梦亦难重续。’决然舍去,中有怨情,故才欲说便咽住。下云:‘隐约遥峰窗外绿。不许临行,私语还相属。过眼芳华直太促,从今望断横波目。’天长地久之恨,海枯石烂之情,不难得其缠绵沉着,而难其温厚和平。”庄棫的《蒿庵词》,是陈廷焯极口推崇为“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的,这四阕《蝶恋花》又是《蒿庵词》中被陈廷焯举为“托志帷房,<SPS=0384>怀身世”的代表之作。这四阕词都是典型的男人说女人话。词中的抒情主角的形象,是那么娇媚幽怨婉转缠绵的少妇,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仕途奔兢的男性官僚,他在“当局”面前有“所谋”,先觉得有“可成之机”,而又“韬光匿采,忧谗畏讥”,终于确有“谗人间之”,致使“伤所遇之卒不合”,直到不能不“决然舍去”,仍然“深信而不疑”,这样一个萦心利禄、摇尾乞怜的老官僚或酸书生的形象,同那个娇媚幽怨婉转缠绵的少妇的形象实在反差太大了。那么可以推想,男人说女人话的必要,或许就是为了美化,为了把君臣之间并不美的关系,披上一套男女之情的美的外衣。这个推想,仍在《白雨斋词话》中便可找到佐证,卷三第四○条云:“西堂《菩萨蛮·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源出温韦,身世兴衰之感,略见于此,而词意不免浅显。如‘负负欲何言,饥来难叩门。’又‘浓笑写官衔,排行无二三。’又‘叹息返柴庐,当门立吏胥。’又‘白发影婆娑,秋风鬼病多。’又‘何物返魂丹,空囊无一钱。’又‘何处度余年,除非离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浑雅之笔,便是飞卿复作。余惟爱其次章云:‘六宫闹扫芙蓉镜,君王偶爱飞蓬鬓。殿脚惜空同,昭阳天几重。江南春雨晚,红豆新歌满。流落杜秋娘,琵琶忆上皇。’读之令人泪下。”所举“全失忠厚之旨”诸句,全是没有说女人话而直发失意的老头的牢骚的,那些形象确实不怎么美。(虽是诗圣杜甫,他的“一饭不忘君”的形象,例如自己吃槐叶冷淘而想到“君王纳晚凉,此味亦时须”之类,一个老头儿想念皇帝,也不怎么美。)而被赞赏的那一阕,所谓“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浑雅之笔”,恰恰是男人说女人话,有了一个美人形象,所以就“读之令人泪下”了。其实,尤侗的牢骚,不过是晚年不得意,而早年曾蒙皇帝赞了一句“真才子”,他就把这么一点“恩荣”女性化为“君王偶爱飞蓬鬓”,把自己的感激涕零女性化为“流落杜秋娘,琵琶忆上皇”,真叫人觉得怪恶心的。
那么,常州词派的主张,是不是只要是男人说女人话,一概都好呢?则又不然。《白雨斋词话》卷三第四七条云:“叶元礼词,直是女儿声口。如‘生小画眉分细茧,近来绾髻学灵蛇。妆成不耐合欢花。’又‘蝶粉蜂黄拚付与,浅颦深笑总难知。教人何处忏情痴。’又‘罗裙消息落花知’,又‘清波一样泪痕深’,又‘此生有分是相思’等句,纤小柔媚,皆无一毫丈夫气,宜其天亡也。”主张“托志帷房”的常州派,却又反对男人说女人话说得“直是女儿声口”,甚至诅咒这样的男人活该早天,这又是为什么呢?正在此时,读到了乔以钢女士的系列论文集《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使我豁然开朗。
《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以下简称《世界》)一书,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自古代至当代的妇女文学,全书充溢着思辨性和艺术性,处处闪烁着理论和智慧的独创性的光,其研究重点是现代妇女文学,但我以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的,尤在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如果说,中国“五四”以来的妇女文学,尤其是当代妇女文学,已经很有人研究过,《世界》一书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非有新见新意不漫然下笔;那么,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除了极个别的如李清照而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作过理论研究(不是说没有人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有之自《世界》一书始。例如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男性作家的思想背景中,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而外,异端的道家佛家常常有复杂的甚至很强的影响,而女作者们受儒家以外思想的影响要微弱得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常有纵深的历史感、恢宏的宇宙意识,而女性作者所重视的只是现时现世的家庭亲族间的人伦情感;男性作家的幻想可以天马行空,弃世绝俗,女性作者即有幻想,也大都偏重情爱的实现,缺乏对现实的否定性的超越;还有书中全面细致地剖析了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诸如此类,都是没有人指出过,如今一指出来又是这么确然至当而不可易的。但是对此我也不打算全面评论,我要说的还是它对我一直在思索着的问题的启发。
《世界》一书中这样谈到“男人说女人话”的问题:“中国历代有许多男性文人曾经拟作闺音,他们将自己的文学触角伸向女性生活、女性情感,有些作品相当‘女性化’,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而且,有些时候,他们对女性命运的透视甚至比女性自己更为清晰、深刻。然而,无论如何,那终归是男子眼中、男子心中的女性,是渗透了男性意识而完成的作品。就反映女子心灵而言,虽然可以相当接近真实,但与女子自己的创作相比,毕竟只能属于赝品。”此书不是专谈这个问题的,所以没有更详细发挥,但是它细致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即真正的“女人话”与男性作者的作品的异同,这就大有助于我们研究男人何以要说女人话,说到什么程度等等。
《世界》一书提出了一个概念:“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我以为是极重要的。书中本来是指女子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女性之别,而其意识中没有灌注以人的质感、人的主体精神,所以那种女性意识只是“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我想,这个概念更适用于“男人说女人话”的场合,用这概念可以清清楚楚地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本来无非是附庸意识、奴隶意识,与性无关,但是用女人话一说出来,这就加以“性化”了,这就可以探索出男人为何要说女人话的道理。另一方面,男人所应说的女人话,并非任何女人话,而只是“性化”了的附庸奴隶之话,这就可以探索出男人说女人话只应说到如何程度的界限。
那么,男性作家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何以需要加以“性化”呢?《世界》书中有云:“士大夫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仕与隐的矛盾,在女子身上是不存在的。她们无‘仕’的资格,也便少些‘隐’的欲念。”又有云:“封闭的环境,低下的地位,把妇女牢牢捆绑在各自所依附的男人身上——即使他远走天涯,即使他早已死去。这种绝对而永久的屈从,使女人很自然地产生了格外注重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的心理。尽管绝大多数女性婚前根本未曾有过恋爱的经历,但这却只是愈加促使她们高度重视既成事实的‘命定’的婚姻,……当她们赖以寄托全部人生的家庭生活、婚姻关系出现种种不合人意的状况时,此中哀痛特别强烈,特别难以忍受”。由此可见,男性作家的奴隶意识,由于实际上存在着“仕”与“隐”、“进”与“退”的选择可能,表现出来就还不是那么“绝对而永久”;只有进入性别关系中自居于对某一个既定的“夫主”的“绝对永久的屈从”的地位,才能使感情表现得专一。孟浩然的“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都惹得皇帝不高兴,就因为其中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负气的意思;如果用女人话来说,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负气话。“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只是女子还相当自由的“三百篇”时代才会有的声音。前面我们说男人说女人话是由于美化的必要,那还是从表现手法上说的;现在我们更补充以把附庸意识、奴隶意识再加强化专一化坚贞化的必要,即意识上的必要,这就更完整了。
另一方面,男人说女人话,又以说到什么程度为限呢?《世界》中有云:“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爱具有狭、深、抑的特点。狭,是指她们受特定生活状况的制约,爱的范围偏于狭隘,基本限于自己的家庭圈子。……当一切都系于家庭,都系于父母、公婆、丈夫、儿女身上时,人生情感在这狭小的河道中奔涌,常是格外深沉浓郁的。而这种不仅基于血缘、婚姻关系本身而且基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来的爱,在特定社会环境、社会意识的统驭下,不少时候其实含有卑贱者对高贵者蛰伏、礼拜的意味,于是,她们的爱又往往显得抑郁而沉重。”我由此想通了,常州词派理论家为什么不赞成男人说女人话说到“直是女儿声口”的程度,就因为“托志帷房”的本意,是要把男子的附庸意识、奴隶意识说得像封建女性的爱那样深沉浓郁、压抑沉重,《白雨斋词话》反复强调词要“沉郁”,要“中有怨情”,就是此意。而叶元礼词中“生小画眉分细茧,近来绾髻学灵蛇,妆成不耐合欢花”等句,则只是有女儿的“纤小柔媚”,没有思妇怨女的浓郁沉重,所以不足取。《白雨斋词话》的自序中指出有一种词的毛病是“美人香草,貌托灵修,蝶雨梨云,指陈琐屑”,正是指屈原以降男人说女人话的“美人香草”的传统,必须寄托有君臣(堂属、主奴)之遇的男性感情内容,那才是虽说女人话而仍有“丈夫气”;而不可以当真像女儿家那样地“蝶雨梨云,指陈琐屑”,那就“无一毫丈夫气”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男性作家虽是对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进行模拟,其实是借取女性话语中的一部分来加强表现自己的一种男性感情,而不取女性话语中的另一部分,那是只足以把男性降低为女性的,卑视女性的心理在这里一点也没有失去作用。
末了要补充说明,《世界》一书的研究重点,毕竟是在当代女作家。我觉得,作者正因为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过深彻研究,所以她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处处可以看出是以古代女性文学为参照系,这就和某些知今而不知古的研究大不相同。这是此书的一大特色,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生逢乱世我们凭什么活着?】
男建女的原因:
1、可以在游戏中获得男性角色的帮助。
2、喜欢女性角色的优美造型,谁都喜欢自己能操纵一个美女进行游戏呀。
3、他可能是G(男同志),这样就可以在游戏中和男性交往。
4、体验做女性的感觉。
女建男的原因:
1、避免被无聊的男性骚扰。享受游戏的乐趣。
2、喜欢男性角色健美的身体,可以为自己喜欢的角色换装。
3、她可能是T(女同志),这样就可以在游戏中和女性交往。
4、体验做男性的感觉。